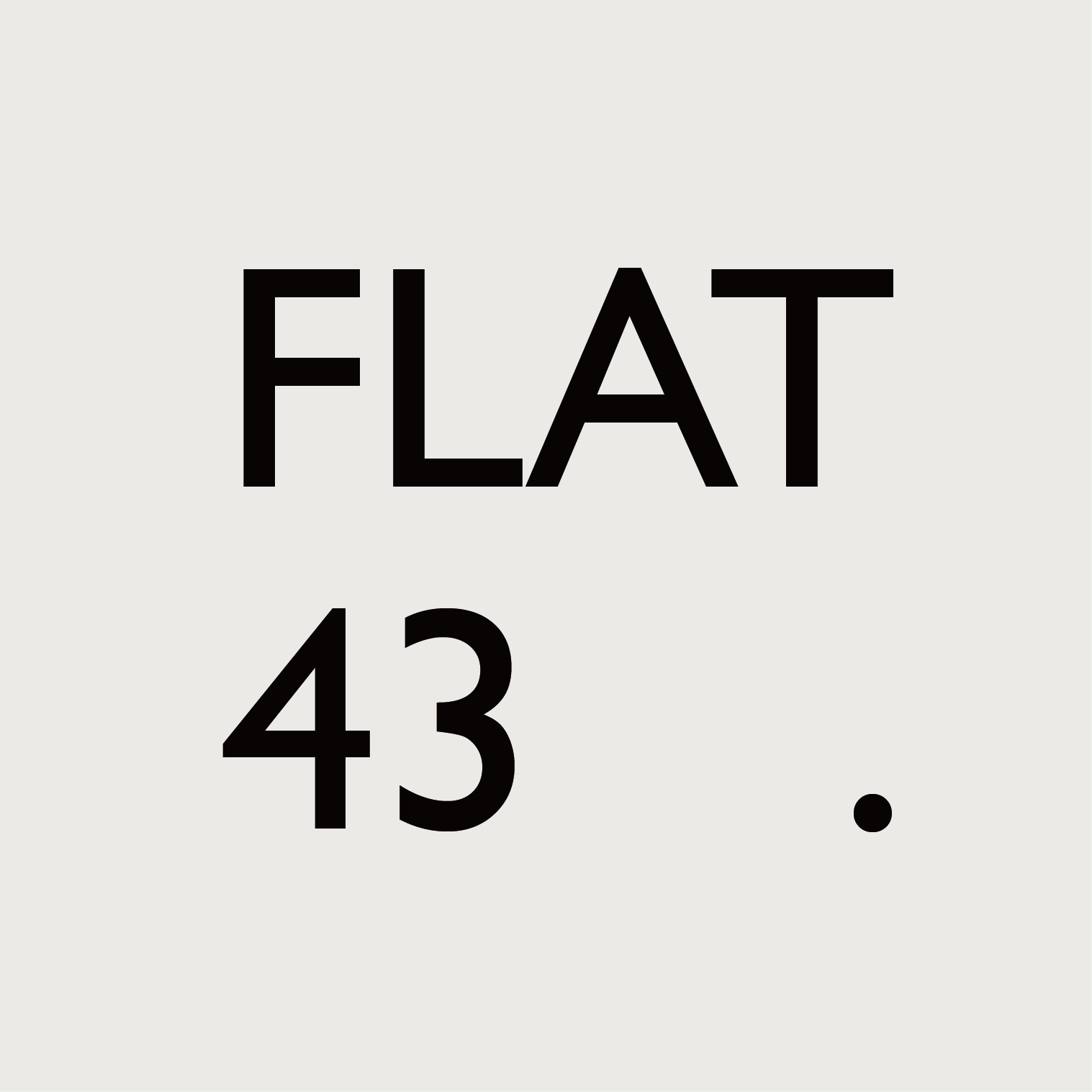2023 е№ҙжҹҗеҖӢйҖұжң«дёӢеҚҲпјҢеңЁеҖ«ж•Ұи«ҫдёҒдёҳзҡ„дёҖй–“е”ұзүҮиЎҢиЈЎпјҢдёҖеҖӢзңӢиө·дҫҶдәҢеҚҒеҮәй ӯзҡ„еҘіз”ҹи№ІеңЁи§’иҗҪзҝ»жүҫзҲөеЈ«жЁӮеҚҖпјҢеҘ№з”·еҸӢз«ҷеңЁж—ҒйӮҠж»‘жүӢж©ҹгҖӮеҘіз”ҹзӘҒ然иҲүиө·дёҖејө Miles Davis зҡ„гҖҠKind of BlueгҖӢпјҢгҖҢеҳҝпјҢдҪ зңӢпјҢ1959е№ҙйҰ–зүҲ!гҖҚеҘ№з”·еҸӢжҠ¬иө·й ӯпјҢгҖҢеӨҡе°‘йҢў?гҖҚгҖҢдёҖзҷҫдәҢеҚҒйҺҠгҖӮгҖҚе…©дәәе°ҚзңӢдәҶдёүз§’пјҢеҘіз”ҹжҠҠе”ұзүҮж”ҫдәҶеӣһеҺ»пјҢдҪҶжүӢжҢҮйӮ„еңЁе°ҒеҘ—дёҠж‘©еЁ‘дәҶдёҖжңғе…’жүҚзңҹжӯЈй¬Ҷй–ӢгҖӮ
жҹҗй–“зҚЁз«Ӣе”ұзүҮиЎҢзҡ„иҖҒй—Ҷе‘ҠиЁҙжҲ‘еҖ‘пјҢзҸҫеңЁдҫҶиІ·й»‘иҶ зҡ„е№ҙиј•дәәпјҢд»–еҖ‘жҠұи‘—еүӣиІ·зҡ„е”ұзүҮпјҢеңЁжүӢдёҠзҝ»дҫҶиҰҶеҺ»зңӢдәҶеҸҲзңӢиӘӘпјҡгҖҢжҲ‘жғіеӣһ家еҶҚж…ўж…ўжү“й–ӢгҖӮгҖҚиҖҒй—ҶиӘӘйҖҷи©ұжҷӮ笑дәҶпјҢйӮЈеҖӢ笑容裡帶й»һз„ЎеҘҲпјҢдҪҶд№ҹжңүй»һзҗҶи§ЈгҖӮеӣ зӮәеңЁдёҖеҖӢд»ҖйәјйғҪиғҪз«ӢеҲ»дёӢијүгҖҒз«ӢеҲ»ж’ӯж”ҫзҡ„жҷӮд»ЈпјҢйЎҳж„ҸзӮәдәҶдёҖејөйӮ„дёҚиғҪйҰ¬дёҠиҒҪзҡ„е”ұзүҮжҺҸйҢўпјҢжң¬иә«е°ұеё¶и‘—жҹҗзЁ®е …жҢҒгҖӮ
еҲ°еә•жҳҜд»ҖйәјпјҢи®“й»‘иҶ е”ұзүҮеңЁиў«е®Је‘Ҡжӯ»дәЎдёүеҚҒе№ҙеҫҢпјҢеҸҲйҮҚж–°еҮәзҸҫеңЁйҖҷдәӣдәәзҡ„з”ҹжҙ»иЈЎпјҹ
е„ҖејҸж„ҹзҡ„еҸҰдёҖйқўпјҢе°ұжҳҜдҪ з„Ўжі•еҝ«иҪүдәәз”ҹ
1877е№ҙпјҢж„ӣиҝӘз”ҹжҠҠиҮӘе·ұжң—иӘҰгҖҠ Mary Had a Little LambгҖӢзҡ„иҒІйҹіеҲ»йҖІйҢ«з®”ең“зӯ’пјҢж’ӯж”ҫеҮәдҫҶзҡ„иҒІйҹіеҫ®ејұгҖҒеӨұзңҹпјҢдҪҶйӮЈжҳҜдәәйЎһ第дёҖж¬ЎжҠҠиҒІйҹіз•ҷдҪҸгҖӮеҚҒе№ҙеҫҢпјҢеҹғзұізҲҫВ·иІқеҲ©зҙҚж”№иүҜдәҶйҖҷеҖӢз¬ЁйҮҚзҡ„иЈқзҪ®пјҢзҷјжҳҺдәҶе№ійқўең“зӣӨе”ұзүҮпјҢд№ҹе°ұжҳҜеҫҢдҫҶжҲ‘еҖ‘иӘӘзҡ„гҖҢй»‘иҶ гҖҚзҡ„зҘ–е…ҲгҖӮйҖҷжқұиҘҝеңЁдәҢеҚҒдё–зҙҖдёӯи‘үзөӮж–јжҷ®еҸҠдәҶпјҢ33 иҪүзҡ„ LP е’Ң 45 иҪүзҡ„е–®жӣІе”ұзүҮпјҢжҲҗзӮәжҜҸеҖӢдёӯз”ўйҡҺзҙҡ家еәӯе®ўе»іиЈЎзҡ„жЁҷжә–й…ҚеӮҷгҖӮ
йӮЈеҖӢе№ҙд»ЈпјҢиІ·е”ұзүҮжҳҜдёҖ件йңҖиҰҒиЁҲеҠғзҡ„дәӢгҖӮдҪ еҸҜиғҪйңҖиҰҒжҗӯи»ҠеҺ»е”ұзүҮиЎҢпјҢеңЁдёҖжҺ’жҺ’е°ҒеҘ—д№Ӣй–“зҝ»жүҫпјҢеә—е“Ўжңғе•ҸдҪ жғіиҒҪд»ҖйәјйўЁж јпјҢ然еҫҢеңЁи©ҰиҒҪй–“ж”ҫзөҰдҪ иҒҪгҖӮиІ·еӣһ家д»ҘеҫҢпјҢдҪ жңғе°Ҹеҝғзҝјзҝјең°ж’•й–ӢеЎ‘иҶ е°ҒиҶңпјҢеҫһе°ҒеҘ—иЈЎжҠҪеҮәй»‘иүІең“зӣӨпјҢе°Қи‘—е…үз·ҡжӘўжҹҘжңүжІ’жңүеҲ®з—•гҖӮ ж”ҫдёҠе”ұзӣӨпјҢзңӢи‘—е”ұйҮқз·©з·©иҗҪдёӢпјҢжҺҘи§ёеҲ°жәқж§Ҫзҡ„йӮЈдёҖзһ¬й–“пјҢз©әж°ЈиЈЎжңғе…ҲеӮідҫҶдёҖйҷЈзҙ°еҫ®зҡ„еҷқеҷқиҒІпјҢ然еҫҢйҹіжЁӮжүҚзңҹжӯЈй–Ӣе§ӢгҖӮ ж•ҙеҖӢйҒҺзЁӢе……ж»ҝдәҶе„ҖејҸж„ҹпјҢиҖҢе„ҖејҸж„ҹзҡ„еҸҰдёҖйқўпјҢе°ұжҳҜдҪ з„Ўжі•еҝ«иҪүдәәз”ҹгҖ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