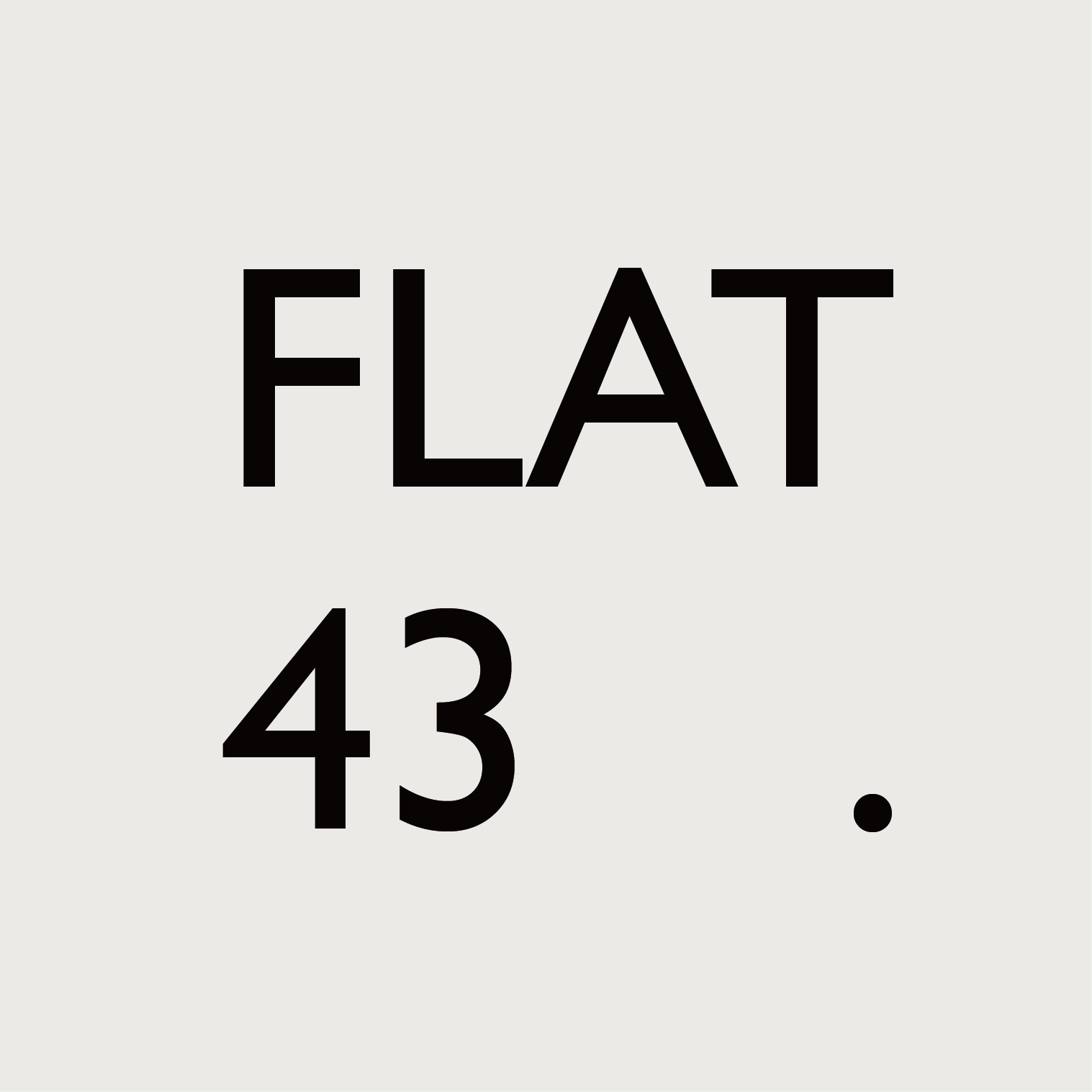從疫情封鎖時打開串流平台那一晚起,開始覺得家裡的空間也能瞬間變成了一種新的銀幕。我們不需要排隊買票,甚至可以中途暫停,影片的音量與字幕都能隨自己喜好變化。
身體軟爛的陷在客廳沙發裡,螢幕上的注意力穿插在字幕、對白、與空間裡殘留的生活感之間,這些屬於自己的個人時光,成為了我們新的奇異氛圍⋯⋯
重返電影狂熱的黃金時期
從詢問朋友「最近有什麼好看的片?」,到習慣性地打開手機 App 搜尋評分與觀後感之間,我們的習慣改變,這中間只過了不到幾年的時間。
來自 Letterboxd 這個原創於紐西蘭的電影記錄平台,本來只是一群影癡工程師設計的觀影筆記系統,至今已累積千萬用戶,幾乎成為一代人對電影觀後的隨手備忘錄。每部片下的短評與標籤系統取代了影評人,變成新的風向參照。貼文、列表、片單、emoji 反應與轉貼語共同組成一種社群型態,讓我們對看電影這件事不再止於觀看本身,也延伸到一種可見的社交身分。
但這並不代表電影失去了它的吸引力。2023年7月,《芭比》與《奧本海默》同週上映,在北美與歐洲引發進戲院的人潮。許多觀眾穿著粉紅色洋裝或黑色西裝進入戲院,只為參與某種情緒濃度過高的群體場面。那週被稱為「Barbenheimer」週末,戲院裡出現難以預測的組合與氣氛,像是短暫重返某個電影狂熱的黃金時期。
影迷並不抗拒走進電影院,他們只是需要一個值得走進去的理由,當疫情改變了社交方式,也同時改變了文化消費的方式。不是所有的電影院都能承受這樣的轉變,像是 Cineworld 在2024年初宣布關閉六家戲院,訊息發布後在影迷社群間被迅速轉發,帶著一種難以歸類的惆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