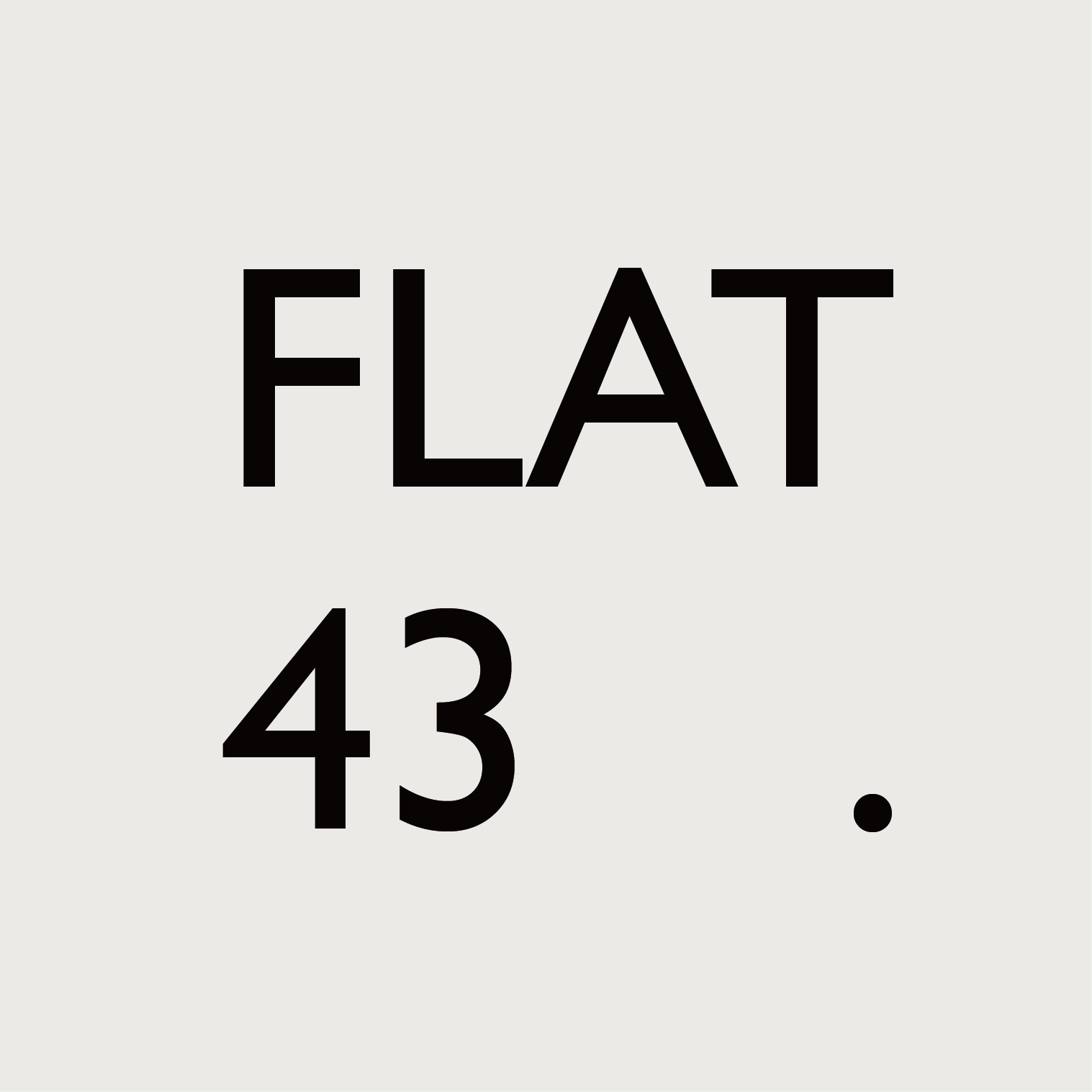┬аТГцу»ЄТќЄуФаућ▒ТѕЉтђЉуџётюІжџЏтцЦС╝┤┬аNeocha┬аУБйСйю№╝їТюфСЙєТѕЉтђЉт░ЄжЎИу║їТћюТЅІтљѕСйютЉѕуЈЙТЏ┤тцџуХЊтЁИтЁДт«╣сђѓ
тйГуеІуггСИђТгАтЮљтюеТІЅУЃџТЕЪтЅЇТЎѓ№╝їтЁДт┐Ѓт░▒ТёЪтѕ░С║єСИђуе«тЦЉтљѕсђѓжѓБТў» 2014 т╣┤№╝їС╗ќуЋХТЎѓтюетїЌС║гуџёсђітцДУдќжЄј iLookсђІжЏюУфїтиЦСйю№╝їтюеУБйСйютЙъС║Ітѓ│ух▒ТЅІтиЦУЌЮуџётЇЃудДСИђС╗Бт░ѕжАїТЎѓ№╝їтйГуеІтЅЇтЙђСИГтюІуЊижЃйТЎ»тЙижј«№╝їТјАУефт╣┤У╝ЋуџёжЎХуЊиУЌЮУАЊт«ХсђѓтюетїЌС║гСИђСйЇуХЊуЄЪжЎХуЊит║ЌуџёТюІтЈІС╗Іу┤╣СИІ№╝їС╗ќтЙѕт┐ФухљУГўС║єСИђС║ЏжЎХуЊиУЌЮУАЊт«Х№╝їт«їТѕљС║єт░ѕжАїсђѓтѕ░С║єуДІтцЕ№╝їС╗ќтЈѕтЏътѕ░С║єТЎ»тЙижј«сђѓС╗ќтЏъТєХжЂЊ№╝џРђю2014 т╣┤уџётЇЂСИђтЂЄТюЪ№╝їТѕЉтј╗ТЎ»тЙижј«ТЅЙС╗ќтђЉујЕ№╝їтЁХСИГСИђтђІ№╝їт░▒Тў»уЙЁжЕЇ№╝їУффУ«ЊТѕЉУЕдУЕдТІЅтЮ»сђѓТѕЉСИіТЅІтЙѕт┐Ф№╝їУђїСИћУд║тЙЌт░ЇжЎХтюЪСИђж╗ъжЎїућЪТёЪжЃйТ▓њТюЅсђѓРђЮтЏътѕ░тїЌС║гтЙї№╝їС╗ќу╣╝у║їжЉйуаћУБйжЎХ№╝їтЙѕт┐Фт░▒У┐иСИіС║єжђЎуе«тиЦУЌЮсђѓ 2016 т╣┤СИІтЇіт╣┤№╝їС╗ќТ▒║т«џС╝ЉтЂЄСИђт╣┤№╝їтЁеУ║Фт┐ЃТіЋтЁЦУБйжЎХУЌЮУАЊсђѓ
┬а
ТѕЉтќюТГАтЁиТюЅСИЇт«ЅуЕЕТёЪуџётЎетъІ№╝їСИђуе«ТљќТљќТг▓тбюуџёуЙјТёЪ
тйГуеІуџёжЎХуЊиСйютЊЂу▓Йуи╗у┤░УєЕ№╝їтЃЁт╣ЙтЁгтѕєтјџ№╝їжбеТа╝у║ќУќёУ╝ЋуЏѕ№╝їуюІСИітј╗ТюЅСИђуе«жђџжђЈуџёжБёжђИТёЪ№╝їжђЎуе«УдќУд║ТЋѕТъюТ║љТќ╝т»гжЌіуџётќЄтЈГтъІжќІтЈБтњїу┤░уфёуџёт║ЋжЃеуџёухљтљѕ№╝їуюІСИітј╗ТўЊТќ╝тѓЙУдє№╝їтЇ╗тЈѕТхЂжю▓тЄ║уЕЕжЄЇУЄфС┐Асђѓ РђюТѕЉтќюТГАу░Ау┤ёСйєтйбт╝ЈТёЪт╝иуЃѕуџётЎетъІ№╝їТюЅтіЏ№╝їСйєСИЇтЁиТюЅТћ╗ТЊіТђД№╝їтљїТЎѓТѕЉтќюТГАтЁиТюЅСИЇт«ЅуЕЕТёЪуџётЎетъІ№╝їСИђуе«ТљќТљќТг▓тбюуџёуЙјТёЪсђѓТЅђС╗ЦТѕЉуџётЎеуџ┐тЙѕтцџт»дућеТђДСИЇт╝и№╝їСйєТў»т»дућеТђДСИЇТў»ТѕЉуџёТа╣ТюгУ┐йТ▒ѓсђѓРђЮ жђЎуе«РђюТљќТљќТг▓тбюРђЮуџёуЇеуЅ╣уЙјТёЪтЙѕтцДуеІт║дСИіТў»тЈЌтѕ░С║єС║їтЇЂСИќу┤ђУІ▒тюІжЎХУЌЮт«Х Lucie Rie уџётй▒жЪ┐сђѓтйГуеІт░ЄтЁХУдќуѓ║тЂХтЃЈтњїжЮѕТёЪТ║љТ│Ѕ№╝їућџУЄ│жѓёуѓ║Тќ░ТўЪтЄ║уЅѕуцЙу┐╗УГ»С║є Tony Birks Тњ░т»Фуџё┬аLucie Rie┬атѓ│Уеў РђћРђћ жЎХуЊиСИђућЪсђѓ
┬а
т░ЇТќ╝ТѕЉСЙєУфф№╝їТЅІтиЦТў»СИђуе«УБйСйюТќ╣Т│Ћ№╝їСИЇТў»жбеТа╝
тюежЎХтЎеуџёУБЮжБЙтюќТАѕТќ╣жЮб№╝їтйГуеІСИ╗УдЂжЃйТў»жЂІућеу░Атќ«уџёуЪЕтйбТѕќжЉ▓тхїУЅ▓уиџ№╝їтЙъСИЇТюЃуЋФуЋФТѕќТЈЈуЋФтюќтЃЈсђѓ РђюТѕЉУфЇуѓ║тЦйуџёУБЮжБЙТЅІТ│Ћ№╝їТў»жЂІућеС║єжЎХтюЪТюђТюгУ│фуџётЈ»тАЉТђДт«їТѕљуџё№╝їТЅђС╗ЦТѕЉжЂИТЊЄтѕ╗уиџсђЂТЅЊж╗ъУђїтЙїжЉ▓тхїу┤ІТеБсђѓРђЮтюежЎХтЎеСИіТЈЈуЋФтюќТАѕТёЈтЉ│УЉЌт░Єт«╣тЎеТюгУ║ФУдќуѓ║СИђуе«УАежЮбуџётфњС╗І№╝їжђЎтљдт«џС║єжЎХтЎеуџётЈ»тАЉТђД№╝їТЅђС╗ЦС╗ќТІњухЋжђЎТеБтЂџсђѓ жЏќуёХС╗ќуџёжЎХтЎеСйютЊЂтцќУДђу▓ЙуЙј№╝їСйєС╗ЇуёХтЁЁТ╗┐ТЅІСйюТёЪ№╝џуиџТбЮтњїт░ЈтГћуџёу┤░тЙ«СИЇУдЈтЅЄТђД№╝їжђЈжю▓тЄ║УБйСйюУђЁуџётЅхСйюуЌЋУиАсђѓСйєТў»тйГуеІСИдТ▓њТюЅтѕ╗ТёЈУдЂтюеСйютЊЂСИіт«Буц║УЄфти▒уџётГўтюе№╝їТѕќуЄЪжђатЄ║У│фТеИуџёТЅІСйюТЋѕТъюсђѓ Рђют░ЇТќ╝ТѕЉСЙєУфф№╝їТЅІтиЦТў»СИђуе«УБйСйюТќ╣Т│Ћ№╝їСИЇТў»жбеТа╝№╝їТЅђС╗ЦТѕЉжЂ┐тЁЇжА»УђїТўЊУдІуџёТЅІтиЦТёЪ№╝їтюеуЏАтЈ»УЃйУ┐йТ▒ѓжЂћтѕ░у▓ЙТ║ќуџётљїТЎѓ№╝їУ«ЊТЅІСйюСйюуѓ║СИђуе«уЌЋУиА№╝їУЄфуёХтю░уЋЎтГўтюеСйютЊЂСИГсђѓРђЮ
┬а
жђџжЂјжЎХуЊит»дуЈЙСИђуе«С║гжЃйт╝ЈуџёухЋуЙј
тйГуеІтюежЂјтј╗уџёт▒ЋУдй РђћРђћсђіТ«ўт┐хсђІт▒ЋтЄ║С╗ќтюежЂјтј╗тЁЕт╣┤тЇіСИГУБйСйюуџёжЎХУЌЮСйютЊЂ№╝їтЁХСИГтїЁТІгтЁГтђІСИЇтљїуџёу│╗тѕЌ№╝їТ»ЈтђІу│╗тѕЌтѕєтѕЦС╗ЦС║гжЃйуџёСИЇтљїтю░ж╗ъТѕќТЎ»УЅ▓тЉйтљЇ№╝џжЄЉжќБт»║сђЂжіђжќБт»║сђЂТИАТюѕсђЂТи║тиЮсђЂТЎџТФ╗сђЂу┤░жЏфсђѓС╗ќУДБжЄІУфф№╝џРђюжђџжЂјжЎХуЊит»дуЈЙСИђуе«С║гжЃйт╝ЈуџёухЋуЙј№╝їТў»ТѕЉтюетЂџжЎХуџётЁГт╣┤СИГСИђуЏ┤СИЇт┐ўуџёт┐хТЃ│сђѓРђЮ сђіТ«ўт┐хсђІжђЎтђІТеЎжАїТ║љТќ╝ТЌЦУфътќ«УЕъ РђюсЂќсѓЊсЂГсѓЊРђЮ№╝їТёЈуѓ║ТЄіТѓћТѕќжЂ║ТєЙсђѓ РђюТѕЉтюеТЌЦТюгућЪТ┤╗жЂјтЁЕтђІтцЈтцЕ№╝їтГИу┐њТЌЦУфъсђѓТѕЉтЙѕтќюТГАжђЎтђІУЕъсђѓС╗ђж║╝СИЇТёЅт┐ФуџёсђЂТѓ▓тѓиуџёсђЂжЂ║ТєЙуџёС║ІТЃЁуЎ╝ућЪС║є№╝їТѕќтцДТѕќт░Ј№╝їжЃйтЈ»УЃйУффжђЎтђІУЕъсђѓтЙътГЌжЮбСИіуюІ№╝їсђїТ«ўсђЇТў»Т«ўуЋЎсђЂТюфС║є№╝їсђїт┐хсђЇТў»т┐хТЃ│№╝їТЅђС╗ЦТ«ўт┐хТў»т░Їтц▒тј╗ТѕќжђЮтј╗уџёС║ІТЃЁуџёСИђуе«ТюфС║єС╣Іт┐хсђѓРђЮ СйєТў»жђЎтђІУЕъС╣ЪТхЂжю▓тЄ║СИђуе«УЄфуёХУђїуёХуџёТјЦу┤Їсђѓ РђюТѕЉУд║тЙЌжђЎтђІУЕътѓ│жЂћС║єСИђуе«тЙѕУцЄжЏюуџёт┐ЃТЁІ№╝їтЁХт»дТў»СИђТЋ┤тЦЌт░ЇтЙЌУѕЄтц▒уџёуљєУДБсђѓРђЮ
┬а
┬а